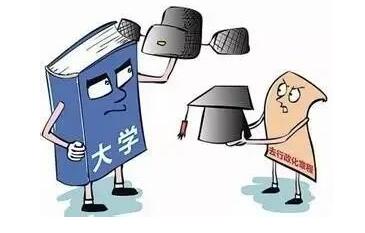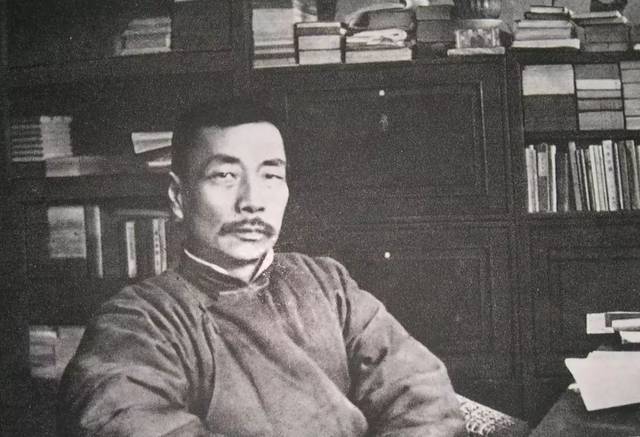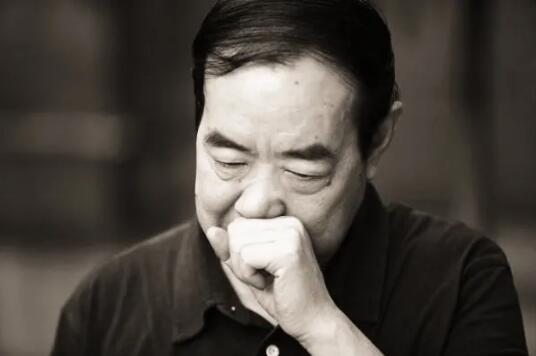手上有一张延安文艺座谈会期间拍摄的照片,其中人物站坐随意,东张西望,表情各异,甚至还有人咬着耳朵在密谈着什么。坐在第一排中间的毛泽东身体向前微欠,面色柔和若有所思。站在最后一排的作家萧军衣襟敞开,站姿笔挺,脸上微有笑意,略显有些落寞不群,与场上轻松欢愉的主色调稍感疏离。从照片里人群的姿态布局看,像是在座谈会间歇时拍摄的,也许他们刚刚从聆听毛泽东演讲的肃然情绪中松弛下来。在名为《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这篇著名演讲中,毛泽东尖锐地提出了文学艺术家在新的空间里应该如何感受生活的问题。呼吁那些从上海亭子间过来的人尽快辨别出“革命根据地”与所谓“大后方”的国民党统治区之间的差异,并尽快适应它。
毛泽东自信地宣称,来自亭子间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应该体会到时代特征的转变。“到了革命根据地,就是到了中国历史几千年来完全未有的人民大众当权的时代。我们周围的人物,我们宣传的对象,完全不同了。过去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在这片民众当家做主的崭新世界里,文学艺术家必须在“人民”中重新安身立命,并以此为目标检验自己的改造程度。在这个群体中不允许有私人的存在,艺术家用不着再去挣扎观望,他们只有一条路可走:铁下心来做无产阶级和人民大众的“牛”,这个“牛”字是从鲁迅“俯首甘为孺子牛”这句诗中引申借用而来。
“孺子牛”是谁?
毛泽东用新发明的“牛论”向坐在台下的亭子间艺术家们喊话,语调明确坚定,坐在底下听演讲的萧军不会听不出其中的深意。他是否同意毛泽东的这套“牛论”,没有明确记载,但从他的日记中可以找到一些其内心波动犹疑的蛛丝马迹,如在和朋友聊天时萧军就苦闷地说,工农革命是为自己的利益,知识分子革命是单纯为了心。可见,在听完“牛论”之后,这些亭子间文人并未马上清晰地找到内心世界与民众身体相结合的切入口。
萧军以为,知识分子投身革命是可贵的也是痛苦的,工农革命受直接的利益所得驱使,知识分子革命却直接导致生活水准降低,往往要以精神和身体的不自由为代价,克服双重的困难。言外之意,让知识分子毫无保留地做工农的“牛”,损失将会是巨大的,他不但要战胜自己,战胜敌人,还要战胜各种诱惑。
由此看来,即使基于民族大义的召唤,勉强服从政治目标的规训,知识分子的心灵是否就能真正得到安置的确让人起疑。对于文学而言,逼迫一个人去歌颂他所认为平凡的东西是不合理的。萧军举例说,陕北人没见过洋楼,看见了杨家岭的办公厅也觉得惊奇,至于在都市住过洋楼的人,他怎能有心情去歌颂它。因为吃过鱼肉的人,对于仅仅吃饱了饭的“幸福”是不会产生兴奋的,这就是劳苦大众和小资产阶级之间的分歧点。萧军深知自己这类满身都是“小资产阶级”气味的作家,在根据地浓厚的政治气氛中必定感到格格不入。在萧军眼里,艺术和政治正如相互试探的情人,只能偶尔亲昵,最终还要分开,是政治吞噬艺术,还是艺术独立于政治,始终是他萦绕于心难以抉择的心结。
有一次读《托尔斯泰传》,萧军觉得托尔斯泰性格中有那种反抗一切既成权威,而要成为一个“王”的感觉,几乎到了无原则的程度,很有些与自己相像。与托尔斯泰的区别仅仅在于,他代表的是没落的贵族阶级,自己代表的是流氓无产阶级、农民以及民族革命斗争的人们,一旦与民众接触就会发生天然的亲近感,这个自我定位不知不觉把自己摘出了小资产阶级的队列。萧军自认这种身份感的产生与父母出生于不同的家世有关,他的母亲是没落的官家女儿,瞧不起平民,父亲是贫苦的平民出身,看不起官家的高贵,自己的性格中同时具备官家和平民的质素,时常激烈地相互缠绕对抗,其中一个终究要杀死另一个,最后的结果是“父亲杀死了母亲”。
萧军曾把身边尊敬的友人和自身对比做过一个粗略的分类,如把毛泽东看作儒家,鲁迅是儒家兼墨家,他本人属于儒与侠一类。有一次和彭真谈话,他说自己身份近于名士与游侠,共产党人以集体主义走向政治的风格近于孔孟,两种风格虽异,人生指向则同。
声明:本媒体部分图片、文章来源于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权,请联系删除 025-8470736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