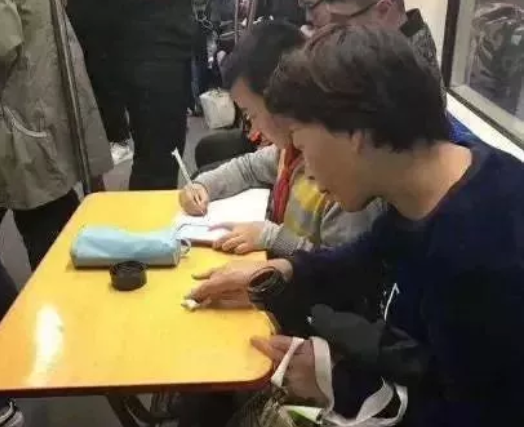在文化结构和文化精神的深层肌理中,文化的超越性本质与文明范式的自在性特征之间存在着天然的紧张。文化作为历史地凝结成的生存方式,从本质上体现着人类对于自然状态的超越与修补,从而达到人的自为与自觉状态,这是人的自由本质的规定性。也就是说文化是人类共同体成员认同的价值模式和行为范式,它对于每个人的行为方式和价值取向具有一定的给定性和内在强制。雅斯贝尔斯坚信,人类有着共同的文化起源和目的。这是因为文化来自人类共同的生存经验和价值标准,任何文化的流变和发展都无法彻底颠覆这一传统范式,人类的文化理性并不热衷于激进主义的文化运动。在文化的长期稳定结构中,文化范式不仅激发人们的自由意志,同时还给予人们更多的理性约束,使得文化的任何变化不至于彻底捣毁传统的伦理底座。人类的精神状态在风雨交加的俗世中由于文化的稳定结构而得以抚慰,文化佑护人类度过无数机警而沧桑的岁月。人类与文化相依为命。由于文化的模式和精神结构得益于长期的历史选择,其中必然为人类的精神安全提供应急通道,不可避免地为人们的行为方式进行文化立法。当一种文化在长期的超稳定生存之后,必然引起文化超越的冲动,这种自为与自在之间的张力是一种正常的发展动力,从而引发文化的发展和流变,以不断适应和满足人们的精神自由。但是,任何文化的发展都无法完全割断传统的脐带,即便有外源性的文化危机也不例外,这是文化自身的安全自卫。所以,文化向来对于任何政治形态的嵌入采取的是一种不信任和排斥状态,以此保证文化生态的平衡和人类经验的传承和持续。
一
文化的稳定结构和发展是对人的行为安全的保护,也是对于政治和制度侵害的抵制,这种紧张有助于在剧烈的制度变革中起到保守消极权利的作用,因此,文化的改造和利用向来被极权主义所看重。与人类生活的物质层面不同的是,文化的变化有着难以估摸的速率,有时表现得极其顽强,很少为外在的强制力量所动,但是有时又异常脆弱,可能在一夜之间随着政治形态而游走。在极权主义看来,影响其政权创立和持久的不是人们的经济贫困和民间暴力,而是稳定的文化模式与精神结构,任何文化的传统都可能构成对于极权主义的抵抗。极权主义的抱负不在于掌握一城一地,也不仅仅在于牢牢地控制一个国家的经济框架,而在于改造人性和控制文化,于是,对于文化的改造和控制是所有极权主义运动的使命。在阿伦特看来,极权主义在控制文化的过程中会想象出一个前后一致的谎言世界,与其说是满足现实本身的需要,不如说是满足了人类思维的需要。通过纯粹的想象和预言,使失根的群众能够感到自在,并在对谎言的认可中弥补对于现实的不足。人们常说历史的发展充满了伤痛和悖谬,其实,历史的发展在许多时候是对乌合之众的惩罚,因为历史并不具有救赎情怀。极权主义并不是历史的选择,而是人们在一定历史时空中犯下的错误为其提供了机会,因此,极权主义历史恰恰是人们的选择。这种选择最先体现在对于文化改造和文化控制的选择,因为文化革命所描绘的谎言激起了人们对于传统的愤恨,只有进入谎言的文化结构中,人们才能感到人生的意义。本来,正常的文化发展和改造不仅来自文化内部,得益于文化的内源性危机,同时,文化的任何变化、变迁、转变和转型都会呈现多样化特征,只有在文化的谎言预谋中,文化的转变才呈现高度的统一性。只有按照极权主义的政治模式建立的文化统一才不至于构成对其政治专制的威胁,文化的力量和无孔不入使任何坦克也束手无策,这就是为什么在希特勒的屠刀之下,犹太人照样有笑声和幽默来讽刺其纳粹运动。所以,任何极权主义运动中,其军事手段仅仅是一种辅助技术,也不是根本目的,文化的专制才是统摄人们精神的主要方式。
在文化谎言的建构中,极权主义首先要割断文化的传统脐带,通过洗脑和宣传把一切文化传统描绘成影响现实进步的羁绊。传统是文化谎言的天敌。文化传统不仅是人类在历史发展中价值系统的凝结,还存储了人们为了保卫生命与自由所沉淀的智慧和经验。传统是文化的慈母,每一个生命在文化传统的眼睛里都是一个成长中的婴儿。希尔斯发现,文化传统作为文化遗产,作为过去留给现在的既定事物,实际上并不能用物理学比喻作出合乎现实的解释。在一些情况下,人们所遵循的传统之所以被广泛接受,是因为在一种需要作出行动的情境中,传统似乎明显就是人们所要求的行动。希尔斯说,“绝大多数人都没有足够的想象力可以想出一种替代既定事物的办法。在身边已经存在某种现存的范型的时候,他们也不会感到迫切需要设想出某种新事物。在合乎既定范型的行动已经显示其功用的时候,这种情况就更加明显”。
人们有想象明天的兴趣,但同样的是,对于传统的想象和神往又是人类精神状态的一大特点,许多人愿意沉浸在传统的“黄金时代”而不愿意直面未来。文化传统的保守理性和务实品质显然制约了文化谎言的构建,如果不切断传统的文化之维,文化的谎言结构就无法展开,并且还能形成对于文化改造的反包围。因此,文化的谎言建构会充分利用人们的人性弱点,尤其群体不具有理性和判断能力的特点,进一步夸大文化传统对于现实的危害。人们的心理状态有时候容易受到新事物的蛊惑,在群体心理中,一切对于旧事物的反对往往容易得到认同。文化传统像一位不动声色的老人,他不擅长使用文艺化的语言去进行动员,只是默默地守护在我们身边。因此,文化传统在激情主义的画卷中容易背负保守与遏制创新的坏名声,甚至把人类社会本身的现实缺陷推倒在传统的身上。然而,文化的传统的确是遏制了理性的疯狂冲动,传统是已有的人类经验,而理性是抽象的,往往与自负结盟。柏克认为,任何建立在传统积累之上的文化模式和制度模式都要优越于乌托邦空想,尤其那些根据空洞的幻想和抽象的推理而进行的文化设计与政治结构是对人类经验的反叛。
文化的传统对于全面的文化改造不仅天然排斥,还具有质疑能力和博弈功能,并且不承认激进主义的文化进步,甚至从一开始就已识破极权主义的文化建造阴谋。对于极权主义声言的文化进步进行批判和牵制,不仅是文化传统的道德勇气,还是其接近真理的品质,因为任何割断传统的文化模式都可能为人类酿成灾难。在资源的争夺中,极权主义与文化传统势不两立,甚至把它看作建立自己专制帝国途中的最大敌人,因此,所有的文化谎言开始随意涂改历史,把每一次历史的进步都说是对传统的抛弃,把每一次历史的转危为安都说成是对传统的割裂。同时,把每一次历史的灾难都说成是对于传统的固守和对于革命的拒绝,他们认为自己的理性已经超越了所有传统,并在理性中找到了千真万确的真理。在极权主义起源的条件中,人们过多地相信了这种激情的历史判断,同时用自己的双手为自己的生命和自由编织了绳索,从而加入了一系列文化谎言的建构。遥远的历史时代和文化传统是理性的人们憧憬和敬畏的对象,并能够用以梳理当下的价值取向,是评判流行文化的行为范式,它的强大的磁场功能能够校正人们的伦理道德和信仰文化。人类天生有一种对于文化传统的信任和依赖,因此,对于文化传统的打碎是文化谎言的第一步,如果不能清除文化传统的影响,文化谎言也就无法建立。如果不把文化传统污名化,也就无法剥落文化传统的魅力,只有如此,才能使文化谎言顺利构筑自己的历史神话。
二
仅仅摧毁文化的传统根本不是文化谎言的终极目的,为了建立文化谎言的统一体系,摧毁传统仅仅是第一步,其次是建立文化的排他性体系。也就是文化谎言建构过程中必须排除其他反传统文化思潮的干扰,然后才能独霸客体资源。在文化的动荡中,对于文化传统的否定和批判并非来自一种阵营,各种革命思潮可能都想占据文化传统退出之后的受众资源,因此,极权主义的文化谎言则必须进行排他性的建构方式。如果一种正常的文化求变思潮,它本身决不会有排他性的暴力行为,因为它本身不具有建立谎言世界的野心。正常的文化激荡会在一种开放的价值体系中与传统展开论战,同时也与当下的文化思潮展开平等对话,只有怀具极权主义目的的文化谎言才不能容忍其他文化冲动的存在。你死我活是文化谎言的显著特征。吉拉斯认为,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与众不同之处,并非由于他们所提出的理论本身,而是由于他们运用这些理论时所采取的方法。就是他们不承认同时代人们思想里的任何科学及进步的文化价值,常常武断地称之为反动的或者“资产阶级的科学”。通过这种排他性的方法,把所有严肃认真的讨论与交流都被他们预先阻止了,因为他们知道,任何思想所吸引的受众资源随时也可能被其他文化所吸走。这并不能完全解释为他们的狭隘和偏见,而是文化谎言建构的整体需要。因此,鉴别是否是文化的谎言只要看它的排他性就足够了,因为任何真正的良性文化都不会以完全排他而使自己获得影响和地位。埃里克•霍弗在研究狂热运动时发现,所有运动都是从同一类人中间吸收信徒,并且吸引到的都是同一类型的心灵,因此他认为,“所有群众运动是相互竞争的,一个群众运动增加多少追随者,就会让其他群众运动减少多少追随者;所有群众运动都具有相互取代性。一个宗教运动有可能会发展为一场社会革命或民族主义革命;一场社会革命有可能会演变成为军国主义或宗教运动”。
在文化的谎言运动开始之后,一方面大力毁灭传统,一方面必须与其他文化运动争夺资源,这个时候,同时代的其他文化思潮会成为自己最大的敌人,因为各种文化争取的都是一些中间派。所以,任何极权主义运动都会把自己的意识形态宣布为人间真理,并且声称掌握了人类历史的发展规律,可以科学无误地设计出人类社会的未来。把自己的理论说成是人类历史迄今为止最完美无缺的发现,这是文化谎言的惯用技法,任何与此不同的文化主张都判定为异端邪说,并与之展开意识形态斗争。
在人类的群体行为中,总有一批人怀着对自我否定的渴望,然后在一种运动暗示中找到虚幻的目标和方向,这类人群有缺少独立判断的个人,也有渴望在新运动中冒险的团体,似乎一切新的运动的展开都可能重新分配权力。文化谎言运动之所以能够在一定的历史节点成功发动并不断壮大,其本身不是谎言有多么高明,而是群体在历史动荡之中的浮躁和功利主义取向。排他性的文化建构使意识形态呈现单一的发展格局,追随者希望顺着新文化的兴起而创造新的历史,统一的文化建构会把其他文化形态宣判为洪水猛兽。这种文化发展的排他性不可能创造真正的文化艺术,也不会产生真正的文化作品,其目的在于对意识形态的垄断。在文化的核心层面,思想是其须臾不可缺少的灵魂,没有独立思想的文化只是一种意识形态的工具,也许对于思想的控制是文化谎言编织的有力手段,尽管对思想的控制是人类最残忍的专制统治形式,但作为极权主义,为了自己的目的,它必须如此。正如吉拉斯所言,他们“以科学的名义仇视思想,以民主的名义反对自由,通过压制与收买,使人类的心灵完全腐化”。如朝鲜金家政权那样,既不完全吸纳苏联的意识形态,也不照搬中国的思想,更不承认人类的普世价值,必须编织自己的“主体思想”,以此拒绝任何同时代的文化影响,从而想永久、稳固地确立金家王朝的文化谎言地位。尽管文化的限制是对于人类本身的一种最为恶性的攻击,但是,极权主义从不考虑人类底线,文化谎言的建设也不会顾及政治伦理和道德良知。
三
进行预言和承诺是文化谎言的动员手段。文化的谎言不仅肆意篡改历史,进行未来社会的设计和预言是它的强项,并承诺所有的追随者可以改变目前的生存现状。对于生存现状改变的渴望是大众心理的人性弱点,这种情况下,一种理想化的预言可以激发起革命的热血冲动。因为摧毁传统,又在当时的语境中严格排他,所以,对于未来的理想承诺是它的文化擅长。文化谎言的未来预言一个显著的特点不是强调个人的主体地位和权利保障,而是夸耀一个即将到来的整体社会或者完美国家。在所有极权主义运动中,一个共同的特点是,未来的预言成为一个群体中“自我”的替代品,这种群体往往由现实当中的失意者组成,他们坚定地相信文化承诺中即将到来的天堂社会。正是对于未来社会的想象和预言,极权主义得以争取到更多的群众和青年,其预言中的“进步”带有一定的诱惑性,其未来社会的承诺也能激起群体心理的牺牲决心。在这种由预言和承诺支撑起来的文化谎言中,任何传统和理性都会成为革命的对象,要么就地消灭,要么实行专政。即便是具有青春气质的法国大革命,也被托克维尔遗憾地认为,它的创新和进步程度比人们普遍认为的要少得多。极权主义运动中的“进步”预言完全以革命的名义践踏人性、生命和自由,
这一切都被解释成为了实现明天的美好预言。
现代政治文明使我们知道,任何文化的发展与进步并不是人为设计的结果,也并非任何国家和精英的规划,反而是远离国家权力的结果。哈耶克指责说,历史学家们有一种习焉不察的教条,误导人心者莫此为甚,他们往往把强大国家的建立说成是文化进化的顶峰,其实这样则标志着文化进化的结束。历史学家的势利有时给极权主义提供了理论借口,因为他们趋媚的是历史整体以及国家的兴衰,而很少关注组成历史主体的个人。斯宾格勒在《西方的没落》中说过,“人类的历史没有任何意义,深奥的意义仅寓于个别文化的生活历程之中”。之所以极权主义在构建文化的谎言中善于预言未来,这不仅是对于传统的否定,还是对于具体的个人的否定。因为保守主义趋向于保守个人的权利和自由,传统也是由个人创造的文化与秩序。建立在现实基础上的文化传统与个体生命息息相关。而预言未来则意味着要创造一个整体的世界,这种来自抽象与空想的社会里,个人的价值被淹没,尚未到来的“未来”肯定无法找到个人的身影,这里只有国家主义、社会主义、民族主义等虚幻的大词。
另外,对于文化的传统遵循会限制政治权力的势力范围,也会规范其运动行为,而预言未来则不需要立法,也没有规范,使得这种文化建构不用付出什么代价便可以进行一系列虚无飘渺的承诺。在保守主义看来,任何意义上的未来,其价值并不大于当下,因为未来具有更多的不可塑性。但是作为极权主义的理想画卷,它认为只有未来具有合法的“进步”性,每个人都必须服从于“未来”的文化设计和社会规划。阿伦特说,“极权主义的这种文化谎言建构只有在常识失效的地方才能大量地侮辱常识。或者面对混乱的发展和完全任意性的衰落,或者服从于最严格的、异想天开的意识形态虚构的一致性,群体可能永远只会选择后者,随时以牺牲个人来作为代价——这并不因为他们愚蠢或邪恶,而是因为在总体的灾难中,这种逃避至少给他们一种最低限度的自尊”。在常识缺失的地方,群众都有着逃避现实的渴望,因为他们的精神无家可归。对于虚构的热衷,也符合人性的本质,有时候,对于现实的逃避和对于明天预言的追随其本身就是对现实世界的判决,弱势心理只有在对预言的服从中才享受到对于现实进行主宰的幻象。
世界本身的不完美造成任何现实世界都会充满缺陷和矛盾,矛盾和冲突是现实世界的真实状态,然而预言中的世界是完美的、没有矛盾、没有剥削,只有天使。这种文化谎言的构建明显在利用人类思维的弱点,让人们在这种承诺之中而付出当下的一切,放弃个人的价值判断和文化主张,然后加入到统一的文化范式之中。别尔嘉耶夫发现,这种状态中的群众不是生活于现实,不是生活于存在,而是生活于事物的表象,尤其愿意生活在一些大词包装之下的幻影之中。这是因为,生活在预言的幻象和文化谎言中远比生活在现实中容易,这样凭着对于预言的想象可以切断人生与现实的关联,然后使自己的精神进入一种宗教般的控制。但文化谎言提供的宗教控制并不提供灵魂栖息之地,在这里,个人没有灵魂独立的文化权利。
四
文化的谎言从来就会把自己装扮成为了人类福祉而进行的一场神圣事业,随着对未来社会的预言和承诺把自己建构起来的文化谎言发展成宗教,或用宗教的手段进一步控制文化的一元状态。正如埃里克•霍克所说的,人们“信仰一件神圣事业,相当程度上是替代已经失去了的自信”。也就是这种对于极权主义意识形态的信仰取决于个人自信缺失的地方,乌合之众是文化谎言信仰化的资源基础,它失败于独立自信的个人。当极权主义的意识形态成为一种宗教之后,这种排他性就具有了暴力统一维持的特点,但与宗教不同的是,极权主义的文化暴力化有自己的武装机器。因此,利诱与恐吓成为它的两面。在利诱方面,文化谎言会设立近期承诺,只要进入这种文化范式就得到了精神拯救,也就是找到了人生的根本方向和目标。自己的生命是有限的,投入到这种神圣伟业中,有限的生命会变得无限。这种精神承诺很容易让原子化的个人遗弃那个飘移不定的“自我”,然后奔向一种天堂般的、明天既可实现的乌托邦理想,人的精神成就于此开始,个人的幻觉开始放大。在一些群体运动和宗教活动中,原子化的个人都希望有一种群体性保护,只要加入其中,原来没有意义和目标的自我已经被伟大的事业所埋葬,在文化谎言构筑的文化空间里,每个加入其中的人都有献身的渴望。除了精神承诺之外,文化的谎言还利用其政治体制设立物质刺激,进入这种文化范式的先锋还会钦定为文化大师和精神领袖,各种激励环节会顺利地把一些乌合之众引入彀中。虽然历史已经证明,任何文化谎言俘获的都是一些社会低劣成员,当然其中也不乏一些聪明之士,但是,短期内的世俗利益承诺和情绪享受仍然使之在每个朝代都有市场,这就是为什么一些邪教能在任何时代出现的原因所在。
在恐吓方面,文化谎言的宗教化会利用一切手段对于其他文化进行封剿,对于任何背向文化谎言的逃离都要进行惩罚。设立严格的文化管制是其常用的手段之一。吉拉斯在考察苏联的文化谎言中发现,这种制度就是窒息并压制任何它自己不同意的求知活动,也就是窒息并压制一切深刻的及富于创造性的东西,然后把自己的文化谎言强加于人。这种制度之下文化管制中的恐怖活动,以禁止其他不同的思想为目的,其惊人的专制形式造成了对人类思想难以置信的压制和摧残。每个渴望思考真理的人在这种严酷条件只能保持缄默,这种“专制统治最恶劣的表现就是在于它强迫人们不要像平常那样去思想,强迫人们表达不是他们自己的思想”(吉拉斯)。这种文化方面的恐吓手段是非道德的与不讲是非的,它不容得对文化谎言进行任何形式的质疑,要求对其保持高度信仰,并坚信它的绝对唯一的真理性。
文化谎言的宗教化并不单方面统一其信徒的文化观,而是从社会的全方位铺开,是从幼儿教育入手的,每一个人从学习语言之初,就必须有核定的文化范式和教育内容,然后延及历史教育,在谁掌握了现在谁就掌握了历史的极权主义语境中,历史已成为谎言的代名词。也难怪柯林武德认为,“一切历史都是思想史”。显然,在青少年中进行文化谎言的构建是极其残酷的,一个人在生命的初始阶段就被剥夺了接受真理的权利和机会。文化的谎言教育不仅是对精神的摧残,还是对人生意义的扭曲,但是极权主义从不在乎个体生命的权利和生命意义的丧失。当一个人在接受了多年的谎言文化灌输之后会形成典型的洞穴思维,这种思维的改变是在他们成年之后吐出狼奶,重新启蒙。但是由于文化的谎言从开始形成的钙化记忆,相当一部分人终生难以相信洞穴之外的阳光,他们宁愿选择在谎言中死去,也不愿再校正自己的记忆,是因为脆弱的灵魂经不起对于失败和欺骗的直视。文化谎言的构建在宗教化的过程中,自然也有自己的仪式、宣誓、口号和徽章,每天重复的口号和符号能够挤走质疑的空间和时间,不断的心理暗示让人保持永久的神圣感和神秘性,从纳粹到布尔什维克都是这种运动宗教化的完成,尤其在民族主义的鼓动下,这种宗教化极易达到顶峰。
文化一旦宗教化之后,不仅形成自己的崇拜方式,还要求其信徒为之殉道,并随时准备着为其奋斗终生。这是文化形式的高度异化,是对人的最残酷的奴役,因为它是从剥夺人的灵魂开始的,失去了自己灵魂的生命已经成为某种文化谎言的工具,甚至成为邪恶的子弹,常常把历史的善意逻辑射穿,或者中断。文化的谎言宗教化是对人的个性的绝对消灭,个人必须自愿服从于这种文化范式所构建的和谐之中。要知道,凡是扬言构建和谐的文化承诺都会是一种谎言,世界的不完满性永远充满矛盾和冲突,人只有在冲突中才能唤醒个人的个性与独异品质。别尔嘉耶夫说,“世界和谐是虚伪的和奴役人的理念,唯有凭籍个性的尊严方能从中解脱出来。世界和谐实际上就是不和谐与无秩序,世界理性的王国实际上也是非理性、无理性的王国”。任何建构世界和谐统一的文化承诺,不是一种唯美主义的浪漫文艺,就是一种疯狂的政治阴谋,必然让世界的自然秩序付出惨痛代价。但是,文化谎言的宗教化离不开这种和谐承诺和实施兴趣,因为只有宗教化才使得显性的暴力统治的减少。
五
文化的谎言建构往往借助极权主义运动在初始阶段的咄咄逼人,其宗教色彩也在短期内可以俘获群体心理,其受众会在这种预言和承诺中达到疯狂。我们常见的邪教以及传销术亦通此理,在这种暗示化的场景中,理性不起作用。但是,人类经验往往能对其进行有效遏制。然而,进入这种文化谎言举国狂欢的往往是缺少政治经验的民族,或者是易感人群。与任何疯狂的群众运动一样,这种文化的谎言则很难持久,它无法长时间统治人心,因为它的善于承诺的长项同时也是它的致命之外,因为时间会检验其疯狂的预言和承诺,在高潮落幕之后,人们不仅要反思当初的道路选择。实际上,波普尔早就告诫过,人类的历史进程是不可预言的,因为人类历史的进程是受到人类知识进步的强烈影响的,我们无法准确地预言人类知识的增长。因此,人类根本无法预言人类历史的未来进程。那些对于人类未来社会模式的预言不是空想,便是包藏了政治阴谋。
经过历史的报复之后,人们不能不去思索人生的根本意义和生命的价值,当人们知道生命被无端葬送在文化谎言之中的时候,对于历史和文化大规模的清算也便开始。也许,有的个体生命根本没有机会加入清算就已经离开了世界,这样的人生便是被谎言彻底覆盖。但是,文化谎言在度过了它的常规期和稳定期之后,造成的文化失范就会迅速凸显文化危机。由于整个社会被文化谎言笼罩多年,其他文化范式被挤掉了成长空间,这种谎言的幕布揭开之后,整个社会陷入一种精神的失重状态。因为文化谎言是一种文化工具化的权力捆绑,其本身不具有文化的内在要素,这样的社会环境中,实际上真正的文化已经死去,一旦文化的谎言撤离,人们并不是暴发出经久不息的掌声。人的深刻奴性和谎言教育的结果,使得部分社会成员呈现出遗憾和虚空,或者面对文化的自由无所适从。这样一来,文化的危机会大面积暴发,特定历史条件下的主导性文化模式已经失范,新的建构尚未全面开始。但是新的文化要素开始介入人们的行为方式,并以自由的姿态清算文化的谎言历史。这种情况下,大部分社会成员,尤其经过文化谎言巅峰的人群痛感人生意义的失败,因为他们从呀呀学语就开始崇拜的偶像和英雄只是一具稻草,人生的荒诞感在瞬间造成了意义的失重。这样就出现了社会成员的多重价值分野,有的开始痛恨历史,有的仇恨社会,有的拒绝未来,有的对于任何文化的精神追求心灰意冷,变成彻底的“唯物主义”者。
这种条件下暴发的文化危机不仅是外源性的,更多的是一种内源性危机,因为目前的文化危机主要来自信仰的缺失和内心的冲突,并不仅仅是外来的新的文化模式冲击了传统的文化结构。在文化的自然生态中,外来的文化模式很难造成民族国家的文化危机,这是因为民族国家有一定的文化稳定结构,文化的免疫功能对于任何外来文化能够抑制、批判或者消化、吸收。虽然,文化的谎言历史时期挤走了传统文化的发展,但是生命中依然有着难以被彻底掏空的文化密码,在文化专制的高压期,它可能潜伏起来,一旦有春风吹动,马上就能激活其成长的愿望。在极权时代的文化谎言模式进入衰退期和变革期之时,最先感到文化失范带来文化危机的是人文知识分子、思想精英,他们要努力用理性和科学把握与引导文化的变化。在这样的危机期,人文知识界必然乱象纷呈,这恰恰有助于文化的健康生态,既有文化保守主义,也有新左派,还有自由主义,也不乏民族主义,几种文化流向固然有自己的利益立场,但其中更多的是对于文化发展真诚的揭示和主张。这种文化危机之中的百家争鸣是文化专制主义的结束,任何文化的一元统一已经无能为力,文化正在回归它的范式常态。虽然在文化思潮中也有为文化谎言叫魂的新文革派,但它毕竟不是文化的主流,也无法吸纳更多的人群,最多只是提供给文化生态一种批判性的食物链,并以此激发文化发展的生命活力。当经过了这种文化思潮反省、批判和冲突之后,一个社会的主流文化才能凸显出来,因为社会大众的接受尚需一定的认知过程。
在社会大众层面,文化危机造成的伦理崩溃、道德框架失散,以及人生意义的缺失是这个时代最显著的文化特征。由于缺少文化对于人生目标的梳理,缺少文化对于人生价值的校正,大众文化主要呈现一种即时消费的娱乐色彩。这虽然是对正统意识形态的消解和疏离,但长期以往,并不能为人生的意义提供有效坐标,也不足以平衡整个社会伦理道德体系。大众文化与群众运动有着相同的心理特点,如果不能在规范的行为内进行价值选择,在一定的条件下会很容易走向它的反面。目前泛滥于整个社会的虚假表情虽然是文化谎言的历史恶果,但同样的是,大众文化缺少核心硬度亦不能逃脱事实批判。因为目前中国语境中的大众文化与西方不同,西方的大众文化建立在强大的精神和价值支撑之上,而中国的大众文化则建立在文化谎言崩塌之后的废墟之上。如果不能有效整合,则始终难以加入文化模式的主流建构。
在体制文化层面,其文化危机表现得充满反讽色彩。一方面其信仰已经被谎言彻底掏空,一方面并没有放下其前辈的文化招牌,这样不仅导致了体制文化的价值怪象,还造成以利益为基础的权力文化秩序的兴起,然后导致其正统意识形态信仰难以挽回的衰落与失败。这种怪异的体制文化面相,扭曲的不仅是体制的精神核心,更重要的是造成权力失去基本公信之后的政治危机。目前的体制文化一方面舍不得放下其正统意识形态文化,一方面又主导德治文化,想以此整合社会行为的失范。然而,在没有放下文化谎言建构模式的情况下,对于德治文化的主导只能进一步加重文化危机,因为德治文化不仅要求法律的外部规范机制,还要求宪政的体制框架,单纯的道德文化根本无法平衡现代权利冲突。杜维明强调,“有了法治并不表示我们一定会形成有道德的社会,在法治的基础上要讲德治,但没有法治讲德治一定有问题,一定会堕落”。因为道德的不确定性很容易成为权力的工具,单纯的道德伦理根本无法遏制权力的信仰危机。在法治缺失的前提下,任何道德文化都可能造成新的文化谎言,我们知道,民主宪政框架中的制度文化是一种消极作为,政治文明会把文化的建构彻底放归文化的自洽生态。因为文化的健康生态中容不下政治的权力之手。目前的中国,文化的危机已经覆盖人心,如何走出这场变革中的危机,单靠揭露和批判是远远不够的,需要我们在清算文化谎言的同时,抛弃所有的先验文化理念,本着生命与自由的首要价值,促进文化的良性转型与重构。
声明:本媒体部分图片、文章来源于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权,请联系删除 025-8470736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