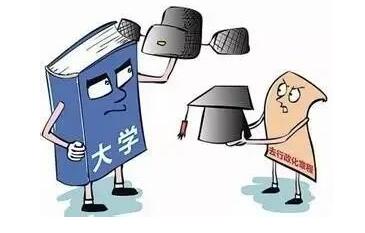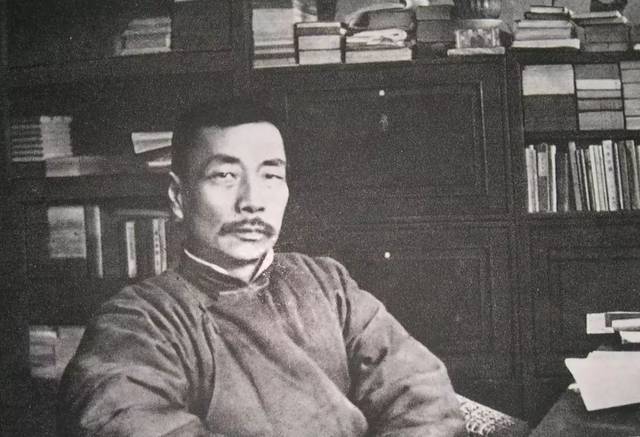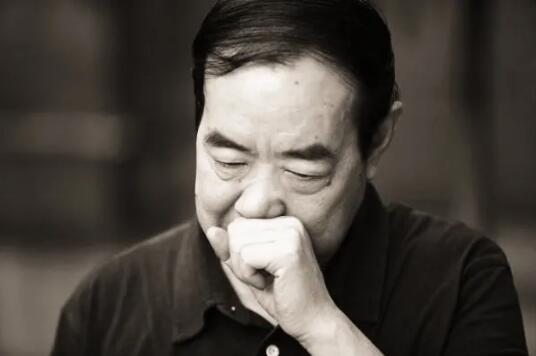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日本小说家大江健三郎(Oe Kenzaburo,1935——)于1957年以短篇小说《奇妙的工作》登上文坛,其后笔耕不辍,半个世纪以来创作中长短篇小说约百部(篇),另行发表了数量更多的随笔、书简、文论、讲演和对谈,作品总字数逾千万字(中文)。大江健三郎借助这些作品置身于边缘,从不停歇地向权力中心提出质疑和挑战,为维护战后和平、反对复活国家主义而殚精竭虑,在日本知识界乃至世界文坛享有很高声誉。
遗憾的是,在大江获得诺奖(1994年)之前,中国大陆地区只翻译了大江第一次访华时写的特约文章《新的希望的声音》(1960)以及三篇零散发表的短篇小说《突然变成哑巴》(1981)、《空中怪物阿贵》(1986)和《饲育》(1988)。译介的缺失不可避免地造成了大江健三郎小说研究的缺失,在此期间,只有王琢的《人?存在?历史?文献——大江健三郎小说论纲》(1988)和孙树林的《大江健三郎及其早期作品》(1993)这两篇论文面世,前者概述了大江“是个举足轻重的‘先锋派’代表作家,在近30年的文笔生涯中,以锐意求新追求与世界文学同步的态势” ,后者则以大江的初期作品群为分析对象,认为“大江健三郎常常走在日本文学界的最前端,用具有现代意识风格的作品去反映忧郁、烦恼、彷徨、无所依托的青年一代,深深地挖掘社会所面临的种种问题以及人生的本质,批判当今资本主义社会的流弊。他的作品被介绍到欧美,成为当今享有国际声誉的为数不多的日本作家之一。然而,在我国,大江健三郎的作品翻译及研究近乎一片空白” 。
及至大江获得诺奖之后,中国的日本文学研究界方若大梦初醒,却苦于没有学术储备,仓促间发表的文章多为动态性介绍文章,这从题名上便可略见一斑,比如蒋白俊的《出人意料的大江健三郎》(1994、12)、许金龙的《超越战后文学的民主主义者——大江健三郎》(1994、12)、叶琳的《日本作家大江健三郎荣膺1994年度诺贝尔文学奖》(1995、1)等等。由于此时国内的大江健三郎小说中译本凤毛麟角,具有独到见解的学术文章更是寥若晨星,因而上述动态性介绍文章所依据的参考资料大多来自日本方面,少见作者本人的独到解读,只能在一定程度上满足普通读者的阅读需求。
在大江获得诺奖后,《外国文学动态》和《世界文学》于1995年1月分别刊载了大江健三郎的两个专辑(含中短篇小说、长篇小说缩译、获奖讲演辞和评论文章等)、光明日报出版社则于同年5月出版了由叶渭渠主编的《大江健三郎作品集》(全五卷,计有《个人的体验》、《万延元年的足球队》、《性的人》、《广岛札记》和《死者的奢华》),稍后,同为叶渭渠主编的两套大江健三郎丛书也相继问世,一套是作家出版社于1996年4月出版的《大江健三郎最新作品集》(全五卷,计有《摆脱危机者的调查书》、《日常生活的冒险》、《同时代的游戏》、《人的性时代》和《青年的污名》),另一套为河北教育出版社于2000年5月出版的《大江健三郎自选集》(全三卷四册,计有《燃烧的绿树》上下卷、《迟到的青年》和《小说的方法》)。应该指出的是,面对解读难度极高的大江健三郎的小说作品,除王中忱等部分译者外,大多数译者并没有相应学术储备,甚至有些译者还是日语专业的在校生,这就使得这一期间的翻译水准参差不齐,部分译本多有误译和漏译之处。
同样是以这批翻译作品为分析文本,部分学者从人类困境和边缘等主题切入,比如叶继宗的《再现人类困境中的不安——大江健三郎初探》(1995、11)、王琢的《“被监禁状态”下的苦闷与不安——论大江健三郎第一阶段初期小说》(1995、12)许金龙的《大江健三郎与中国文学》(2001、5)等等。
由于大江健三郎获得诺贝尔文学奖这一契机,新闻界和书刊界产生了巨大的市场需求,有关大江其人其作品的评述和翻译犹若井喷之状,显现出一派繁华景象。尽管译本的翻译质量不尽如人意,评述亦多为动态性介绍文章,却终究彻底改变了“近乎一片空白”的尴尬境况。尤其在2000年9月,大江健三郎获奖后第一次以诺奖得主身份访问中国,这也是新中国迎来的第一位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在大江健三郎与黄宝生、陈众议、许金龙、王中忱、于荣胜等学者和莫言、铁凝、阎连科、余华、徐坤等作家进行学术交流的同时,出版机构也被激发出更大热情,在其后数年间陆续翻译出版了大江的诸多小说和随笔。这一批翻译出版的最大亮点,即在于开始出现大江当时的最新长篇小说,比如《燃烧的绿树》和《空翻》,而且翻译工作也是由郑民钦、杨伟等年富力强的学者承担,这就为学界及时提供了可以信赖的参考文本,随之出现了霍士富的《大江文学的宗教理想及其在作品的表现——试析<燃烧的绿树>》(2001、9)、许金龙的《一部拷问灵魂的力作——评大江健三郎新作<空翻>》(2003、8)等研究文章。值得关注的是,这是我们在有关大江健三郎小说的翻译和研究方面第一次勉强跟上国外同行的节奏。
有了前十年的积累,发展期的大江健三郎小说研究大致呈现出以下几个特征:
(一)在惯性作用下,仍有诸多学者关注存在主义与大江健三郎小说的各种关联,比如安徽的《继承与超越——论大江健三郎与萨特的存在主义》(2004、3)、兰立亮的《从<死者的奢华>看大江健三郎对存在主义的接受和超越》(2005、2)等等,这些研究者试图从多角度论证大江健三郎小说与存在主义之间密不可分的联系,个别论者甚至断言大江健三郎小说无疑是存在主义的产物。与此同时,也有少数论者在分析大江健三郎小说时,注意到存在主义与人道主义之间的关系,比如蔡志云即在《<空翻>对存在主义的超越及其人道主义思想》(2006、3)一文中指出“大江对存在主义的超越,表现出大江关注人类生存、追求世界和平与和谐的特殊的人道主义思想”,董晓娟更是在《“战斗的人道主义”》(2011、4)中指出,“‘战斗的人道主义’思想贯穿了大江创作的始终”,许金龙也在《大江健三郎文学里的中国要素》一文里表示,“始自于少年时期的对鲁迅的阅读和理解,使得大江不自觉地接受了鲁迅文学中包括与存在主义同质的一些因素,从而在接触了萨特以后几乎立即就自然(很可能也是必然)地接受了来自存在主义的影响。当然,在谈到这种融汇时,我们必须注意到另一个不容忽视的重要因素,那就是萨特的自由选择和鲁迅在绝望中寻找希望的有关探索,其实都与人道主义传统有着密不可分的内在联系,而学生时代的大江在学习法国中世纪经典名著《巨人传》的过程中,也从恩师渡边一夫教授那里‘接受了决定性的影响’——人文主义思想。顺便说一句,在法语中,人道主义和人文主义都是同一个词汇——humanisme。” 相较于萌发期,发展期的这一类论述显然要全面一些,部分观点更是首次提出。不过,这一时期有关存在主义的研究所参考的分析文本多为早中期旧作,未能及时消化和有效利用同期被译介到中国来的大江健三郎小说的最新译本,在相当程度上滞后于日本同行的研究,而且对人道主义/人文主义的论述也不够充分和准确。
声明:本媒体部分图片、文章来源于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权,请联系删除 025-8470736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