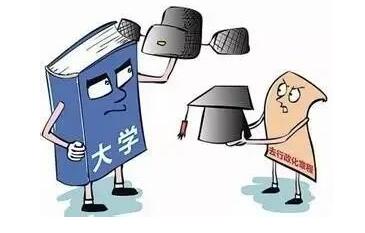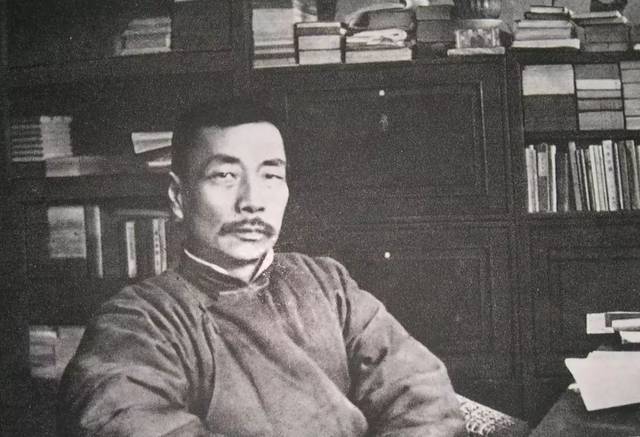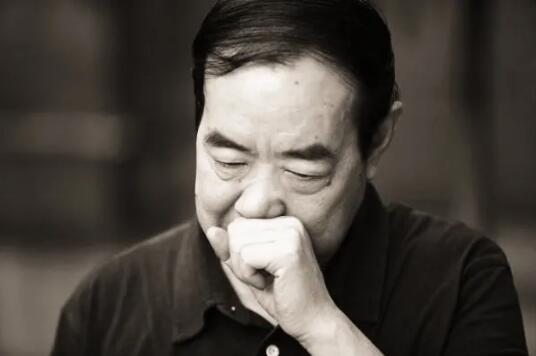(二)互文性在大江健三郎小说中不断呈现出新的样式,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从大江的处女作《奇妙的工作》(1957)开始,直至最近刚刚发表的长篇小说《晚年样式集》(2013),在这跨越半个多世纪的创作生涯中,鲁迅文学一直是大江健三郎创作小说时的重要资源。当然,我们在做如此评述时,同样无法忽视大江健三郎小说中来自但丁、拉伯雷、布莱克、叶芝、本雅明、艾略特、爱伦?坡、本雅明、萨特、劳里等作家、诗人和哲学家的养分,以及来自包括孟子、毛泽东等中国思想家、政治家的积极影响。
在这近十年发展期中的一个可喜现象,就是通过研读大江健三郎小说文本,中国学者不断发现其中的互文关系,其中徐旻的论著《重复中包含着差异》(2011、5)注意到了大江健三郎的部分小说与其对应的西方作家或诗人,用图表列示出《新人吧,醒来啊》与布莱克、《致思华年的信》与但丁、《燃烧的绿树》与叶芝、《愁容童子》与塞万提斯、《别了,我的书!》与艾略特等等对应关系。张文颖的《来自边缘的声音——莫言与大江健三郎的文学》(2007、1),指出无论在文学理念还是写作手法上,莫言与大江健三郎都有着极其相似的地方,而且这些相似之处基本上都包含在边缘世界中。的确,借助莫言和大江健三郎这两位作家或夸张、或幽默、或哲理、或荒诞的描写,最为边缘的女人常常显现出极大的韧性和力量以及勇气,她们敢于与恶劣的生活环境抗争,敢于在绝境中通过反抗寻找希望,从而在一定程度上消解甚或颠覆中心和权力,试图创造出更具人性的新宇宙。也正是因为这种文学观与价值观的共鸣和契合,大江才在不同场合表示“很长时间以来,莫言先生一直是我予以高度评价的、世界文学的同时代作家” ,表示“莫言先生的小说经常会给人很光明、向着希望前进的感觉。我觉得饱含对人的信任这一点是我们文学的首要任务,而表现出确信人类社会是在从漆黑一片向着些许光明前进则是文学的使命” 。
此类中国视角的论文还有杨玉珍的《论沈从文与大江健三郎原乡追寻的美学建构——以河流/森林为表征》(2006、9)、刘东明的《再现生存困境的思索者——大江健三郎与史铁生哲学意蕴之比较》(2007、4)以及许金龙的《“始自于绝望的希望”——大江健三郎文学中的鲁迅影响之初探》(2009、11)等,另有刘军凯的《性、政治与救赎——劳伦斯与大江健三郎创作之比较》(2007、12)。从以上统计中可以看出,中国学者更关注中国作家与大江健三郎小说之间的互文关系,这里恰恰也是外国学者难以深入的一个独特空间,就这个意义而言,我们完全可以期待中国研究团队在同类研究中居于世界前列。
(三)在这后十年的发展期内,中国对于大江健三郎新近创作的所有小说和部分随笔都能在第一时间内翻译并出版,比如《奇怪的二人配》(全三卷,包括《被偷换的孩子》、《愁容童子》、《别了,我的书!》)、《二百年的孩子》、《优美的安娜贝尔?李 寒彻颤栗早逝去》、《水死》等长篇小说(其中《别了,我的书!》中译本获得鲁迅文学奖优秀文学翻译奖),以及《在自己的树下》、《宽松的纽带》、《康复的家庭》、《致新人》、《大江健三郎讲述作家自我》、《读书人》等长篇随笔,无论是翻译种类之多还是出版速度之快,都远远超过世界上任何国家和地区,基本与大江健三郎的创作速度同步,以至大江本人感叹道:“我的小说被翻译成外文,首先始于英译、法译、还有德译,而现在,则被最迅速、最全面地翻译成中文,我对此感到幸福和光荣。” 在这种背景下,以大江健三郎最新小说为分析对象的研究文章的篇数也大幅上升,比如许金龙的《“只将你的心扉,向尚未出生的孩子们敞开!”——解读大江健三郎新作<被偷换的孩子>》(2004、2)、《发自边缘的呐喊——再读<愁容童子>》(2005、11)和《“愁容童子”——森林中的孤独骑士》(2005、8)以及《盘旋在废墟上的天使》(2006、9)、张景韬的《大江健三郎封笔之作<别了,我的书!>》(2006、10)等等。多视角和多维度的论述,在改变中国的大江健三郎小说研究的严重滞后局面的同时,也极大地丰富了我国的大江健三郎小说研究,使其大致可与日本学界保持同步,尤其在《水死》研究的个别领域甚至遥遥领先。在日本保守势力正以越来越快的速度侵蚀战后民主主义成果并快速复活国家主义的当下,大江健三郎借助《水死》以及《晚年样式集》等系列小说作品不断在绝望中发出含着希望的呐喊,中国学者对大江健三郎小说文本中的这声声呐喊进行深度解读,不仅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更是在传达令世人振聋发聩的警示。
发展期内还有一个新变化——大江健三郎应邀成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名誉研究员之后,外文所近年来不定期地在北京、台北和东京等地举办了大江健三郎文学研讨会,邀请大江健三郎本人和台海两岸部分作家以及多语种文学专家出席会议并发表论文。这其中的多数论文以大江的最新译本为分析文本,比如有陈众议的《童心新说——评<愁容童子>与<堂吉诃德>及其他》、《真实与虚构——大江文学想象力刍议》和《逆水行舟——大江文学思想蠡测》、莫言的《大江健三郎先生给我们的启示》、叶渭渠的《大江健三郎文学的传统与现代》、阎连科的《“大江文学”给中国当代文学的几点启示——在中国“大江文学研讨会上”的发言》、吴岳添的《大江健三郎——当代杰出的人道主义作家》、李永平的《回归与拯救》、《反抗中的希望》和《历史忧思与启蒙的冒险》、陆建德的《互文性、信仰及其他——读大江健三郎<别了,我的书!>》和《诗与社会——略谈大江健三郎与威廉?布莱克》等等。上述拥有西葡拉美文学、日本文学、法国文学、德国文学、俄罗斯文学、中国文学、英国文学、比较文学、哲学、美学等学科背景的学者和富有创作经验的作家,运用自己的专业知识,成功地对大江健三郎小说的不同侧面做出了独特解读。他们在为中国的大江健三郎小说研究贡献一批高质量论文的同时,也隐然成为这个研究群体中可以期待的一支优秀团队。
声明:本媒体部分图片、文章来源于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权,请联系删除 025-8470736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