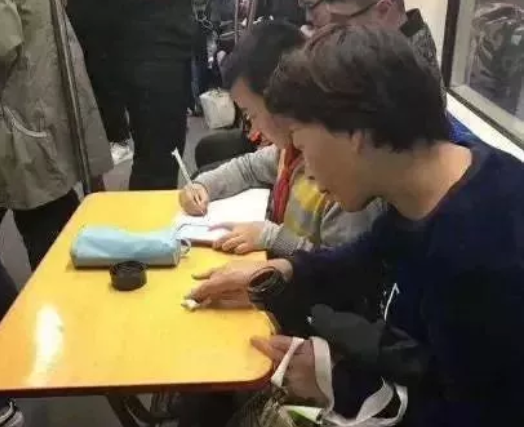中国知识界的精英主义未熟先老已经是一种悲摧的事实,信仰和认知能力的先天不足,导致他们无法像自己说的那样生活。知识精英本来应该像克尔凯郭尔说的那样,“你怎样信仰,你就怎样生活”。但是任何缺少了生命原初澎湃力量的人,已不具有承担当下的勇气和能力,对于哲学王的模仿终究也是一种蹩脚的想象。无论是呼唤告别革命,还是对于秩序的保守,都不是直面现实的开拓,仅是知识老化之后的技术空转和虚荣。
人是被抛的。被逐出伊甸园之后的人类面临了巨大的恐惧与虚无,自然的瞬息万变才被生存压力转化成知识。科学的话语体系和主体的客观性的陈述成为知识的必要条件,这都需要共同体内部达成可以验证的共识。它的目的以人类最根本的价值取向为依归,从而必须符合生命的要求。因此,生命成为任何知识真伪的唯一试纸,而不是知识本身。只有生命才是知识的裁判,而不是相反。也就是无论任何知识体系构筑的如何庞大,编织的如何精巧,它的目的还是围绕着生命本身。正如鲁迅在《华盖集》中所说:“我们目下的当务之急,是一要生存,二要温饱,三要发展。苟有阻碍这前途者,无论是古是今,是人是鬼,是《三坟》《五典》、百宋千元,天球河图,金人玉佛,祖传丸散、秘制膏丹,全部推倒他。”这就说,人首先要生存,然后是温饱与发展,扼杀这些生存价值的知识必须滚开。我想这是知识的初衷,也是知识当初确认的模样,任何知识应该是人之成为人的有效工具而已。
但是,从知识的诞生开始就出现了知识王,解释世界、主宰世界、预言世界也成为知识精英的欲望。本来,任何知识的形成都缘于人类共同的试错和经验,并必须在不断变换的语境中进行检验。纯粹理性判断是在应然意义上的参照,它并不能代替实践理性中的现实判断。可以说每一天所发生的事实,都在提醒知识假定体系防止固化,现实冲突也在预防知识体系的老化,以免知识成为生命的奴役。只有活生生的现实才是知识之母,知识精英应该改善现实而不是领导现实,知识精英的美德就是节制。休谟说,理性是并且应当是激情的奴隶。权力意志是生命的不竭动力,理性往往是知识的结果。无论是哲学王还是贩夫走卒,都无法摆脱生命的基本特征和要求,没有人能够逃出这种生命本身的既定性。所以,检验一种知识的是否有效,或者检验其是否老化还是已经僵死并不是多么困难,只要看它是扩大了生命的自由空间,还是压制了生命的合理要求即可。
知识在发展过程中很容易转化为技术崇拜,一旦形成技术崇拜势必将现实中的生命要求消融,从而走进一种精致的形而上学或者技术垄断。以此拉开与芸芸众生的距离。知识在脱离普通生命之后建立了自己的话语体系和科学体系,以此指导和预测人类的生活。人类历史以来,的确不能离开知识精英的伟大作用,但是知识的技术崇拜很容易形成精英主义,从而不再克制自身的领袖冲动,陷入一种理性的自负:偏执地为人类设计未来,或者进行各种乌托邦构想。
近些年有一个常用的词就是“专业训练”,意味着一种专业的能力和资格,同时也意味着对专业利益的保护和封闭。这样一来,只有“专业训练”的人才有资格在某一“专业”内发言,实际上拒绝了生命本身的表达冲动,进入了一种专业游戏。专业细分化之后,知识精英的自负开始高度自恋和迅速膨胀,不断靠技术理性推导出的假定系统无限扩大为文化霸权,从而获得一种阶级快感。在此情况下,一些知识精英以“专业训练”的名义蔑视来自生命与现实的检验和质疑。这些知识精英认为只有他们才掌握了通往真理的钥匙,没有经过“专业训练”的人不具备探讨真理、自由与设计未来的权利。
中国当代知识精英主义根本不具备自负的条件,一方面没有粗壮的知识气质,当代的知识体系只是一种技术移植,而没有本土原创和文化构建,所以缺少了发自知识本身的骄傲,只是一种表面化、翻译腔的炫耀;一方面文化体系的历史呈现了断裂状态,任何嫁接即便再精巧,也不具有西方知识诞生的文化底色和精神背景,只是一种表情化的低级模仿。虽然儒家也是精英主义的,但是当代儒生已经辱没了儒家的本义,不但无法加入现代政治文明构建,而且在内圣方面也已滑落为世俗主义的利益合作。可以说,当代知识精英主义尚处于皮毛状态,本可以在自己的土地上依靠历史的教训进行自泪开拓,但是,稍一起步就沦为了精巧的利己主义者,并急于同大众和暴民划清界线,从而进入一种专业的、神秘的、纯粹的、安适的知识游戏。这种先天不足一是因为真正传统气血的断绝,一是因为投机主义挥舞的利益橄榄。这样一来,中国的知识精英主义就无法落地行走,既没有福柯的洞见,也没有萨特的勇气,更没有中国古代文士的耻感。他们不想体证自己的乌托邦,只是想让大众成为他们的使徒。
然而,中国当代的知识精英主义是不甘寂寞的,由于先天精神不足无法进入形而上的玄思,虽然一直在梦想贵族化自身,但哲学王并不为其降临这一荣耀。终究禁不住利益中心的诱惑,必然想训导大众,并欲图领袖时代。尽管有异质文明的熏染,骨子里还是想“为万世开太平”。这种自授的正义逻辑意味着天已降大任于他,他因掌握了“知识”的权力就可以用“知识”规训人们的生活。其实,在后极权社会,学院已经不再是真理的城堡,而成为学术垃圾的工地,因他们必须每天接受教学量化的权力训导,其知识生产并不具有现实意义的承接。但由于生存中的恐惧,他便以拥有文化权力的盾牌而傲视大众,本质上是现实权力的合作者。本来,精英主义又是极权主义的早期状态,它极易导向极权统治,是开放社会的敌人。在一个缺少超验信仰的社会,知识的高度技术化之后,它一方面用“专业”话语神秘化绝对化自身,对自己进行权贵意淫;一方面又总想启蒙、领导大众,只是稍一行走,便露出了奴才的底裤。
对于纯粹知识的迷恋是精英主义的本性,这也并没有什么过错,因为现实世界也需要一个纯粹的知识体系。但是中国当代知识精英主义的自恋并非出于对纯粹知识的迷恋,而是一种认知能力和智识缺陷。由于过早离开了大地,已经没有兴趣谛听蚂蚁的歌唱,心目中只有五彩斑斓的凤凰。他们根本听不懂福柯的声音,知识分子应该在道义上反对来自任何政权的一切暴力,然而对于反抗极权的暴力不能在权利意义上放弃。告别革命有一个重要的前提,就是现实权力具有民主的诚意和图谱,并已具备告别革命的法治框架和公民社会基础。否则,任何知识移植只是一种语言游戏,它忘掉了知识产生的语境和它当初面对的敌人的品质。每个人都不愿继承历史的仇恨,都愿意与历史有个切割,但这往往是知识精英主义的一厢情愿。现实的顺沿逻辑并未忏悔自己的历史之恶,奥斯维辛之后,有一种偏执依然在疯狂生长。因此,还是赫伯特的回答掷地有声:“永远不宽恕,因为你无权以那些人的名义来宽恕,那些倒在黎明之前的人。”
声明:本媒体部分图片、文章来源于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权,请联系删除 025-8470736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