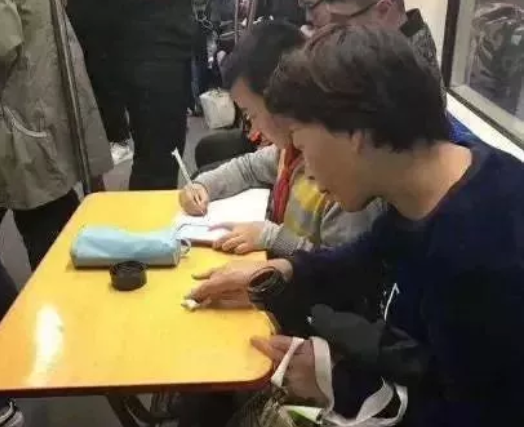托尼·布莱尔说:“社会主义的道德基础是唯一经受住了时间考验的东西。这种社会主义是基于一种道德上的判断,即人与人之间是相互依赖的,他们对自己也对彼此负有义务,良好的社会支持该社会中个人所作的努力,共同的人性要求每一个人都有一块立足之地。这一社会主义的概念需要一种政治形式,以此我们共同承担责任,既向贫穷、偏见和失业开战,以创造条件真正建设一个国家:容忍、公平、富有创业精神和包容能力。”
这样的话语,与奥巴马的宣誓何其相似乃尔!英美两个国家的左倾转向,非常明显,无需过多的辨析,可为人们感知。
至于法国的左派意识形态之影响整个国家的政治倾向,是一个无需太多口舌就可以确证的事情。执政的法国社会党,一以贯之地以其左倾的做派,对法国左翼激进主义发挥着推波助澜的作用。奥朗德是一个政治经验很少的左派政治家。“扩大带薪假期、削减法定工作时间、扩大社会保障,一系列‘社会主义’措施正是奥朗德心目中亟待恢复的‘法国梦"。而谁都知道,法国的问题恰恰是社会福利太多,激励工作的措施太少。不过左倾的法国政府从来不考虑财富来源,只重视财富的分享。这是社会党前总统密特朗就已塑型的法国左倾政治风格。
发达国家的左转,是被宪政体制规定了限度的政治变化。因此,发达国家左转的极限,也就是中左而已。否则,发达国家就不得不处理政体重构的严重问题了。起码到目前为止,这样的政治局面尚未出现。但这种左倾政治的浮显,无疑与发展中国家的左转,构成一幅国际政治普遍左转的总体政治画面。
转轨中的俄罗斯,大有重回左倾激进政治状态的势头。俄罗斯与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的对抗,引人瞩目。普京认为华盛顿规划的世界新秩序毫无前途。真正有价值的是“国家主权的神圣原则”。这种政治主张,正成为普京在国内游刃有余地进行政治动员、获得民众极高支持率的重要支柱。
东欧拉美亦不例外
中东欧前社会主义国家,大多因为经济发展困境,出现明显的左转现象。转轨初期,这些国家多由右派政党执政,因此,在无力扭转经济发展颓势的情况下,纷纷丢掉政权。
由于欧债危机久拖未决,去年以来,罗马尼亚、匈牙利、斯洛伐克和捷克等中东欧国家的经济麻烦不断,部分国家经济甚至出现了“二次衰退”。为了走出经济困境,政府都实施了严苛的财政紧缩政策,增加税收,压缩公共开支,减少社会福利和养老金,造成失业率高涨,普通民众的生活质量受到严重影响。由于中东欧国家政府在这一时期都是右翼政党执政,他们的支持率因此大幅下滑。而左翼政党凭借提振本国经济、改善民众生活的竞选纲领,以及加强政府调控、增加就业机会、促进社会平衡的政治理念赢得民心。
至于上个世纪曾经创造了发展奇迹的拉丁美洲,整体的左倾,已经不是近期出现的事情,而是近十几年的整体政治趋势。拉美在上个世纪后半期创造经济起飞奇迹的时候,就已经由左倾的“依附论”将其打入了不健康发展的深渊。果不其然,拉美在上个世纪结尾阶段陷入了困境之中。由此,对新自由主义的外部批判,就趁势而起,将国家发展陷入困境的原因,归咎于西方帝国主义的、自利的新自由主义方案。于是,国有化运动兴起并兴盛起来,作为对付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侵害拉美利益的趋同性选择。左派政党轻易地赢得国家权力,并且采取激进的经济政策,与发达国家、尤其是美国直接对抗。传统的极左政权及其领袖人物,成为拉美的政治楷模,新生的左派领袖对之顶礼膜拜。古巴、委内瑞拉、玻利维亚的极左体系,巴西、阿根廷、智利、墨西哥的左倾政府,牢固地掌握国家权力。拉美与世界其他地区的左派国家形成了更为紧密的经济合作关系,甚至在政治上也刻意凸显拉美的左派立场。曾经由军人政权主导的拉美经济腾飞,一下子转变为左派政党专政的拉美格局。
与转型国家和曾经迅速发展的国家的左转不同,世界上存在一些自二战以后一直处在极左政治局势中,尚未发生任何改变的左倾激进国家。亚洲坚决抵制现代转型的朝鲜,堪称代表。拉美的古巴,则是另一个老牌极左国家。尽管菲德尔·卡斯特罗退出了国家的领导岗位,劳尔·卡斯特罗努力推动改革,但总的说来,古巴还是世界左派人士向往的代表性国家。
声明:本媒体部分图片、文章来源于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权,请联系删除 025-8470736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