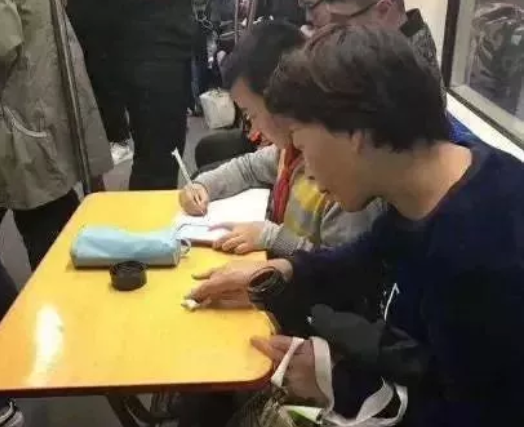利益政治是现代政治的常态
利益原则对于政治的损害常常令人痛心疾首,许多受过良好教育,有着高尚情怀的人常常将罪过认定为利益本身。认为正是欲望本身使得政治和生活变得贪婪、自私、丑恶。于是他们在大声谴责和鄙视利益的同时,把希望寄托于人类的自我克制或者道德感的提升,并热切地寻找各种各样的可资教化人类的信仰体系和道德律令,以及清清白白的政治强人,并试图革新或者创造新的教化方式和体系。倘若这种冲动只在知识分子和理想主义的社会行动者中弥漫,也就不足为怪了。但这种冲动如此普遍,以致几乎成为整个精英群体的某种共识,虽然他们指定的信仰不尽相同,甚至相互尖锐冲突,但他们对于病症的判定却惊人地一致。在自由的网络世界,端庄的电视媒体,高雅的大学讲堂,乃至街头巷尾的标语口号,到处都充斥着类似的抱怨和高蹈的号召。虽然这些抱怨往往仅仅停留在口头,并未真正左右他们的行为,但这种见解的虚伪性并不能抵消其重要性。在人类历史上,虚伪、表面的意见战胜真实深刻的见解,这种景象并不少见。
然而,将罪责归咎于利益本身,或许并不恰当。消灭和压制人们对于利益的追逐的指望恐怕也很难成为现实。因为与古典时代不同,利益已经成为现代社会生活的核心和关键,而这一点,无论人们喜欢与否都很难改变。在经济学家和唯物主义者看来,甚至整个人类的历史都是围绕着利益展开的,个人、阶级、民族都在尽量地使自己的利益最大化,只是人们计算利益的方式,或者遮掩自己对利益的热爱的能力不同而已。这种看法多少有些偏颇,在古典时代,无论是东方还是西方,不管是因为生产方式的原因,还是因为民族性的独特性,人们通过对荣誉的崇尚,通过宗教、政治和道德学说,成功地将利益压制在非常有限的范围和很卑微的地位,利益虽然无处不在,但却很少获得正当性,更不用说支配性地位了。孟德斯鸠曾经这样概括各个民族的立法精神:“扩张是罗马的目标;战争是拉栖代孟的目标;宗教是犹太法律的目标;贸易是马赛的目标;太平是中国法律的目标;航海是罗德人法律的目标;天然的自由,是野蛮人施政的目标;”在他看来各个国家的治理有着各自不同的目的。随着现代社会到来的,如果说它不是现代社会的标志的话,是个人的正当性的获得。个人权利成为一切政治和秩序的基础,而个人利益既是个人权利的外在表现,也是个人保障自己权利的手段。虽然深刻的哲学家们尖锐地指出这是对“个人”和“权利”的误读,但并不妨碍它的流行和有效。因此,追逐和捍卫及的利益,并将之最大化在现代社会拥有无可置疑的正当性。在个人之上,人们结成不同的集团,在国家范围内利益集团之间围绕着利益的分配展开争夺,不同的政体只是提供不同的制度和方案来给这种争夺提供平台和规则。正因为每个人都只是自己利益的捍卫者,因此,人们很难从根本上指责别人的利益主张,也很难分辨哪些集团的利益更为正当,而哪些利益是需要压制的,也没有人或者机构被赋予这样的权力,或者拥有这样的地位,被认为是超越于所有利益之外,可以来做出仲裁和判断。所有的利益都有充足的理由公开伸张自己,寻求与别人的、别的集团的利益相互博弈。正是因为这个原因,世界上各个国家之间的差别也正在不断缩小,无论是在旧大陆,还是新大陆,或者古老的亚洲,民众都在为福利而战,而所有的执政者都不得不迎合民众对于福利的欲求。而且在所有这些地方,利益也深刻地渗入人与人之间的相互关系,法律的精神也为之改变。这仅仅是从观念和我们对其他国家的观察所得出的结论,如果说这种观念在中国还只有短暂的历史,其作用还多少令人生疑的话,那么如果从现代社会的生产逻辑来看,可能会更有说服力。现代社会的一个重要特征是对自给自足的生产方式的毁灭,每个人的生存都需要交换才能维持,复杂的生产和交换体系,使得经济生活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无论是时间还是精力的分配,的地位都大大提高,同时也使得交换无处不在。所以社会的生产和人们的生活一刻也离不开利益的交换。利益关系成为人们最重要的关系,利益的分配也成为人们最关心的问题,这也就不足为奇了。无需我们更多地阐发,这已是每个受过教育的人耳熟能详的常识。
当然,在当代世界和我们的现代历史上,也曾经成功压制人们的利益诉求,以宗教、民族主义的意识形态来实现对民众的动员,对国家的整合,而且在短期内甚至可以取得巨大的成效。但与此同时,整个社会也付出了巨大的代价。这些民族因为其敢于牺牲,不计利害或许能成就惊天动地的伟业,但往往在最基本的社会生产上束手无策。这样的国家既很难长期压制民众的福利要求,也无法在列国竞争中获得有利地位。
最后,任何有经验的政治家都知道,“当我们能够自由地顺从天然秉性之所好处理事务的时候,就是我们把事务处理得最好的时候。”虽然我们很难说,中国人的天然秉性是按照利益的方式处理问题,但如果我们认为中国人天性在于对世俗生活的热爱,在于人情事理的通达,这大概是不为过的。我们从未有过严肃的宗教生活,现代的研究也证明,所谓“存天理,灭人欲”的杀人礼教,实际上对我们的传统的极大误解。改变人们的这种习俗,是伟大政治家常常会产生的梦想,但它并不总是会成功。因为它必定引起社会极大的混乱,比如文革。
基于上述理由,我们不得不说,那些主张恢复党的政治性,打通党与群众联系的努力,或许有些浪漫和自负。也是对于改革以来中国政治和社会的变迁,缺乏充分的理解的结果。
所以真正问题不在于压制和消灭人们对于利益的渴望和捍卫,而在于如何捍卫自己的利益,如何处理利益的冲突,以及如何限制利益集团的争夺对于政治和人心的伤害。
处理利益冲突与驯化利益
虽然无法逃避利益,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只能接受利益的摆布,像丛林里的野蛮人一样地弱肉强食。我们需要的只是,处理利益关系的能力和手段,以及恰当地驯化利益的途径。然而正是在这两个方面,我们表现出了与我们的政治组织能力完全不相称的幼稚和无能。
当利益的剃刀在实用主义的指挥下将整个社会分解之后,我们所面临的正是一个个原子化的个人。强大的政府非但不能实现有效的治理,有时还会发现自己成为所有矛盾的焦点。因为它必须仲裁所有的矛盾,并为其后果负责。在现实中,尽可能地平息事态成为政府最现实的选择,也是它最本能地选择。在这一点上,司法部门,无论其独立与否,都无法真正有效地为政府分担责任,甚至也不能使社会矛盾的解决更为公正,更易为人们接受。司法部门反倒会因为频繁的执行难和不断地上访,而使法律的尊严受到嘲弄。平息事态的思路无论对强者还是弱者都可能造成伤害,因此也不可避免地遭到强者和弱者共同的抱怨。甚至有时我们都无法分辨强者和弱者,比如城管和小贩,弱者常常利用自己的武器改变不利处境和力量对比。事实上,没有法律的保卫,每个个人在内心深处都觉得自己已经或即将成为弱者,8小时之外的官员,去医院看病的患者,正在供孩子上学的家长,概莫能外。而每当人们面临冲突的时候,所有的人都会想到找政府,认为政府应该对此负责。他们这样做并不意味着他们信任政府,而只是他们应该为他们负责,而且政府足够强大。无论是知识分子们的观念争执,企业巨头的商业纠纷,还是街头巷尾城管与小贩的冲突,或者征地公司与拆迁农户的冲突,我们惊异地发现没有人和组织有能力和意愿在发生利益冲突的时候,成立组织,相互谈判,制定规则,并有执行规则的能力。一旦离开政府,任何冲突都有可能引发仇杀和混乱,医患之间,本地人和外地人之间,商业大鳄和以理智自负的知识分子也会像街头的流浪汉一样无助和充满戾气。也正因此,我们时代会产生许多了不起的枭雄式人物,他们能成就令人惊异的成就和炫目的财富,但却见不到伟大的公民,连一个都没有。没有人凭借自己的理想或者愿心,建立一个组织、一个学校,甚至哪怕一座寺院,甚至没有人能以公民的身份对他人产生影响。这种社会自治能力的缺乏,注定所有的人都要依靠政府,同时也必定会抱怨政府。而政府一方面疲于奔命,一方面不得不扩大管理范围和加强自己的能力,事实上,面对这样的社会状况,再庞大有效的政府也会觉得自己不够强大,永远也不会。这些分散的个体足够弱小,没有挑战政府和秩序的能力,但他们也足够坚韧,使得任何试图动员和制服他们的努力,都变得极为困难。
声明:本媒体部分图片、文章来源于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权,请联系删除 025-8470736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