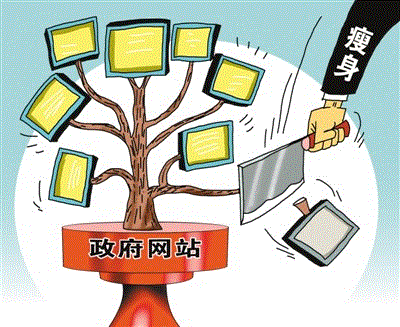这一趋势表明近几年来中国社会结构性风险的升高。这些移民者普遍对他们的财产安全和将来的社会经济走向表示担忧。
这种规避对于中国本身而言当然是极其不利的,因为这些人如果留在体系内部,或许能够构成一种改革的压力,而一旦伸出体系之外,则基本无法影响改革进程。
当代中国的一个重要现象就是传统术数等传统命理学和道观、佛寺香火的复兴。这当然是传统策略的一种复兴。这种复兴绝不是近年来国学热的一个插曲。
例如近年来“四库全书”的很大一部分都在标点和重印,但术数类几乎整套重印则是一个颇让人意外的独特现象。
当然,在当今世界的知识体系中,“命”学早已经无法登上大雅之堂,术数的复兴也并不能说明中国传统文化的复兴,但传统命理和佛道的复兴确实能反映当今社会尤其是精英阶层对于中国式风险的一种焦虑。
这种焦虑的一个原因在于,西方既有的社会理论,特别是风险社会的理论,无法对当代中国的风险社会的遽然兴起做出合理解释,或者即使可以从学理上解释,却无法在个人情感层面消除不确定感,于是,这种极大的不确定感造成了无法满足的知识需求。
中国式风险社会的另一个不容忽视的后果就是社会情绪和心态。如果说,精英层还可以比较奢侈地从传统中寻找安慰的话,底层面临无法规避的风险就不可能如此从容。
不安全感和不确定性发展到一定程度,特别是当全社会意识到这种风险分布的体制性,就会形成一种普遍的受害者心态:仇富、仇官和对公权力及官方话语的不信任。
这是因为人们在作出判断时,主要依据的是自身的处境和社会心态,再基于相似或者对立的原则想象他人的处境和心态。
例如最近几年讨论较多的“空气特供”,也许并不属实,但社会普遍倾向却认为是真的。又如去年的“抢盐风波”,更反映了民众心理深层次的不确定感。
各种风险群之间的心态,进一步导致了一种社会意识的极端分裂。这种分裂表现在不同层次和类型的精英之间,但更体现在精英和社会底层之间。
在分歧严重且相互怀疑的“风险群体”之间寻找共享的价值和目标,自然就变成了一件天字号难题。
社会面对无法逃避风险的最终策略是集体抗争,甚至暴力。如果说不合理收费和突击检查等还可以通过贿赂的方式来规避,但明目张胆破坏规则的、掠夺性的风险转移,无论是以整顿秩序、维护稳定还是经济开发的面目出现,最终都可能激起社会的集体行动。
近几年多起环境问题引发的大规模群体性事件就是一个最典型的例子。结构性风险正如一个长期债券,无论你怎么“重构”(restructuring),无论你将其偿还期限延得多长,最终也会有偿还的一天,而且还得连本带利一起偿还。对于个人而言也许还能规避,对于整个国家和社会却没有办法再作转移。
管理高风险社会
从某种意义上看,高风险社会是中国经济政治体制设计的基本预期。1990年代中叶的经济改革,大体形成了一个中央集权化、地方竞争化和社会市场化的全民发展动员体制。
这种体制下的中央政府掌握了国民经济的关键环节和可支配财政资源的大半,因而具有极强的应付危机能力。
历数这十几年来的各类重大危机,例如1997年的金融危机,1998年的洪涝灾害,2002年的“非典”危机,2008年的汶川地震,2009年以来的全球金融危机,目前体系确实都能比较有效的应对。
如果我们把经济停滞看作另一个最大的结构性风险,那么这个体系的基本表现也是可圈可点的。
这种应付总体性危机的制度,现在却要面对很大程度上是自身造成的各种日常化的社会风险和危机,以及更大的总体性危机。
众所周知,中国现在的“高风险社会”其最大的风险并不是国家的存亡或者经济的崩溃,而是市场化所带来、涉及基本生活质量和生活环境方方面面的风险。
这种风险又极不对称地强制性分配到抗风险能力较差、声音也最为微弱的社会群体:中小企业、社会底层、年轻一代以及子孙后代身上。
这些风险发展到一定程度就会导致抗争行为,进而影响社会稳定。现在国家为维稳所支付的成本,在一定程度上正是在为这种分散在社会各层面尤其沉淀在底层的系统风险买单。
声明:本媒体部分图片、文章来源于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权,请联系删除 025-8470736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