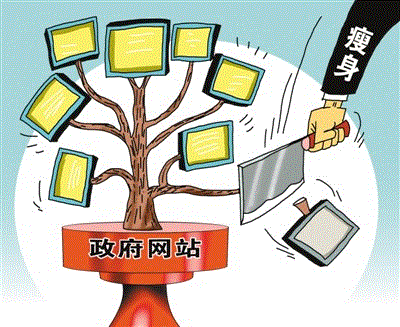在中国历史上,象征性权力与实际权力或名与实之间在许多情形下若即若离或松散关联(loose coupling),这是帝国治理逻辑的一大特点。我们可以从不完全合同和剩余控制权角度(Aghion & Tirole, 1997; Dixit, 1996;周雪光、练宏,2012)对非正式制度的产生和延续给出一个解释:因为委托—代理关系特别是信息不对称性引起的交易成本,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间无力制定严密完全的合约;即使完全合约可以制定,但事后监管的成本昂贵,无法有效实施。
因此,地方政府在执行过程中的实际权力很大,即剩余控制权更多地放在地方政府手中。上下级委托—代理关系有着不完全合同特点,无法将所有情况及其对策明确写入“合同”并有效实施。在上述情况下,有关信息、监督、考核的交易成本急剧上升,实际控制权不得不更多地转向有信息的一方,即地方政府。这意味着,帝国体制中同时存在两种权力,即正式(象征性)权力与实际权力(实际控制权)。
帝国体制的一个鲜明特点是,这种实际控制权从来不是通过上下分治的正式制度(如联邦制)来实现的,地方政府的剩余控制权只能以非正式形式实施,因为这一权力在名义上(正式制度上)属于中央政府。
正因为此,上述的正式与非正式制度间关系实是中华帝国大一统体制的逻辑结果:一方面,地方政府在实际过程中的非正式权力建立在自上而下授权的合法性基础上,依赖于委托—代理的组织制度(周雪光,2013b);另一方面,皇权象征性权威的稳定性得益于地方政府因地制宜地执行自上而下指令方略的灵活空间。
我们不难想象,一统的各类指令方略难以适合于辽阔、多元国土,它们之所以得以执行而不受到挑战,正是因为在各地得以灵活执行从而没有引起不合时宜的质疑。皇权的实际行使受到帝国逻辑的制约,不得不依赖于象征性权力与实质性权力之间若即若离的关系。
因此,这种实质性权力呈现出非正式的但同时又是稳定的状态,体现在一整套稳定的、制度化的非正式行为中,如普遍存在的变通和共谋行为。非正式制度盛行意味着国家正式制度倾向于“名”的象征性意义,而地方政府灵活性有着“实”的意义。这是一个“以名代实”的阶段。
然而,名与实的平衡点是不稳定的。在没有稳定制度保障的条件下,名与实的若即若离为中央与地方关系笼罩了深深猜疑的阴云,即地方政府的非正式权威可能会无节制地蔓延,与帝国中心渐行渐远,从而形成对帝国统治的威胁。象征性权力与实际权力间边界及其背后的控制权关系需要通过其他机制来不断地重新确认、规范和强化。正因为此,名与实之间关系还有第二层意义,即皇权可以不时地从象征性权力转化为实质性权力,有能力(暂时地)令行禁止、抑制非正式运作的蔓延,重塑中央权威之名。
这是一个皇权“以实正名”的阶段。中央政府权威在“以名代实”与“以实正名”之间的转化,形式上的一统性与实际上的灵活性在官僚体制上下级间关系放收松紧之间不断变更调整。唯有“名”之神圣方能允许“实”之下放,给予非正式制度更大空间。一旦“名”之不正,非正式制度成为一统体制威胁,则诱发强化集权的努力。这正是“名与实”这对概念关系的精髓所在,也是上述正式与非正式制度间关系的重要前提。
中央权威在名与实间的转换是帝国治理的重要机制,舍此则帝国架构难以为继。所以,帝国在历史过程中发展起了一系列制度安排和机制对地方政府权力加以层层节制。(吴宗国,2004;周振鹤,2005)在当今国家治理的实际过程中,我们不难观察到名与实间转换的各种机制。
其一,在政策制定和执行过程中,中央政府在宏观层面提出大政方略,但把具体的细化责任、权力交给了中间政府(省市县),把贯彻实施的灵活性放在了基层政府手中,如林权改革过程(贺东航、孔繁斌,2011)、村庄选举(周雪光、艾云,2010)、项目制实施(折晓叶、陈婴婴,2011)。在这一过程中,中央权威经历了“以名代实”,而地方性权威由名到实(即从代理人到实际权力拥有者)的演变过程。
其二,上下级权威间可以通过组织注意力的安排和调节来转化正式与非正式间的边界。例如,在一些情形下,官僚体制通过正式文件传达、检查部署、考核指标、人事安排等机制来调动下级部门的注意力,凸显正式规则、任务环境的重要性;但在另外情形下,自上而下的工作部署表现出落实环节缺位、检查验收权下放等做法,为非正式行为敞开大门。这些做法的交替运作微妙地调节着上下级关系在名与实间的边界。
声明:本媒体部分图片、文章来源于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权,请联系删除 025-8470736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