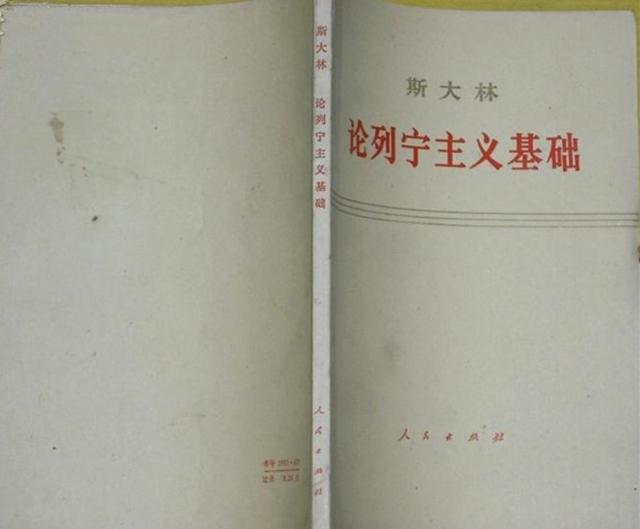更颇值深味的是,在中国,尽管存在文化激进主义与文化保守主义的纷争,但是拒绝与西方宗教价值系统对话,却是其中的一致之处。前者将“形而下”的希腊罗马文化提升为终极关怀,后者则幻想在中国文化的源头上重建终极关怀,但是却都仅仅承认产生民主与科学的西方希腊罗马文化这一源头同时又坚决拒斥真正提供了西方文明价值意义的希伯来文化那一源头。
问题的出现让我们想起了生物学中的“米亚德现象”:两个亲本杂交后,在后代身上却只有一个亲本的性状,没有杂交优势。中国出现的这一取向也可以称之为“米亚德现象”。我们知道,中国文化只有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两个维度,人与灵魂的维度则素所缺位(中国从来就是禅诗相融,但是却没有提出“以诗代禅”这恰恰说明禅之非宗教属性)。因此以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维度的关照物去僭代、假冒人与灵魂的维度的关照物,则是中国文化的公开的秘密。
遗憾的是,所缺明明就是宗教,百年来的引进西方文化却偏偏回避宗教,而且千方百计地要取代宗教。当有人提出西方的进步与宗教相关,中国的落后却与无宗教相关,蔡元培先生就曾武断而言:西方“于宗教何与?”百年来,“宗教”在中国完全就是贬词,几乎与“迷信”划上等号。堂堂中国,没有人敢以不懂科学为荣,但是也没有人不敢以没有宗教信仰为荣。而且,这里的宗教,完全就是针对西方文化中的基督教的。“以美育代宗教”之外,还有“以哲學代宗教”、“教育可以代宗教”、“以科學代宗教”、“以道德代宗教”,所针对的,都是基督教。在梁启超看来,没有上帝中国不但仍能取得进步和自强,而且,中国正是因为没有基督教,才更可能尽快迎头赶上西方。所谓西方"宪法加耶稣"."宪法加孔子",就是他的理想。这样,在上个世纪初,从中国的第一代文化精英开始,借助于与西方基督教文化的对话以弥补中国文化人与灵魂的维度的历史缺位的历史契机,就令人遗憾地与中华民族擦肩而过。
然而,20世纪中国文化历史进程的根本缺憾也恰恰在此。民主与科学犹如两棵参天大树,确实有移植古老中国的必要,但是必须看到,基督教文化却是它们生长的土壤。一般把大树与土壤割裂开来,淮橘为枳就是其中的必然。五四之后八十年来,几经周折,民主与科学在中国依然没有扎下根来,道理在此。
更何况,基督教文化绝非洪水猛兽,西方文化中最值得我们警惕的,倒恰恰是与基督教文化对立的技术至上的物质主义和否弃基督教价值的虚无主义。这意味着:基督教文化的存在是一个必须面对的问题。尽管社会的发展使得宗教信仰的领地遭到侵蚀,但是人类生存的有限性决定了宗教存在的不可替代性。为什么在西方最具理性精神的科学家往往都会归依宗教?为什么在美国既最具现代性但又最具宗教性?为什么在全世界尽管科技发展了但是宗教信仰却仍旧没有衰弱?保罗•蒂里希说宗教是文化的一个维度而不是一个方面,这无疑是非常重要的。这就是说:如果没有宗教,那么所谓文化就是平面的而不是立体的,也就是没有纵深的。
而在20世纪的中国,我们看到的却偏偏就是平面的文化。它的必然结果绝非仅仅是凯撒成为凯撒,而是凯撒成为上帝。而当凯撒成为上帝的时候,世界也就沦为凯撒的意志。这样一来,彼岸成了此岸,超验成了经验,宗教也就成了迷信。
“适应的宗教”
事实上,宗教之为宗教,不仅是西方得以存在,而且也是人类得以存在的根源。关于宗教,人们引用最多的是马克思的“宗教是人民的鸦片”的名言,但是其实更值得注意的应该是另外一句话:基督教是适应的宗教。“适应的宗教”乃是马克思对宗教的准确概括,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宗教才是“鸦片”,因为它不可或缺。而在资本主义社会尤其如此,因为,它是资本主义这个“无情世界”的唯一“感情”,也是资本主义这个“沒有精神的狀态”的唯一的“精神”。
推而广之,对于马克思所谓的“适应”还应该做更为深刻的阐释。上帝可以死亡,但宗教的意义不会死亡。这因为,宗教首先是一种文化形式,一种符号形式和思维方式,首先是人性的“一个扇面”,人类走向自由的“一个阶段”。
简而言之,“宗教”(神)首先是“宗教性”(神性),是一种终极关怀。这因为,宗教实际出于人之为人的无法心安理得。如果能够心安理得,就不会有宗教(神),更不需要宗教性(神性),因为人类自己就是神。而倘若无法心安理得,情况就完全不同了。由此可见,所谓“适应”,更主要的是对于人性的“适应”。维特根斯坦曾经感叹:令人感到神秘的,不是世界怎样存在,而是世界竟然存在。而在此几百年前莱布尼茨也曾经感叹:“为什么有一个世界,而不是没有这个世界?”“竟然存在”与“为什么有一个世界”是这个世界所永远无法说清的部分,世界怎么会从无到有,永远也无法说清,能够使人心安理得的,只有宗教。同时,人生有限,大自然只塑造了人的一半,人不得不上路去寻找那另外一半。这样,人生不是乐园而是舞台,何以来?何以在?何以归?心何以安?魂何以系?神何以宁?这一切同样永远也无法说清,能够使人心安理得的,仍旧只有宗教。而宗教的应运而生,正是对此的深刻体验。在此意义上,任何形式的宗教信仰都是被逼出来的,都是面对解释不了而又必须解释的困惑的结果,都是对于人与世界的关系的根本把握、根本理解,并且通过这一根本把握、根本理解从无序、不合理、无意义走向秩序、合理、意义,从平面、平凡、无意义、单纯走向非凡、立体、意义、厚度,并求得精神支撑。
换言之,假如科学面对的是必然的世界,哲学面对的是可能的世界,宗教面对的就是偶然的世界,一切都不可理解,一切也无可理喻,这些困惑在经验的层面都无法解决,但是在精神的层面却必须解决。宗教所提供的,就是这一解决。它是不可理解的“理解”,也是无可理喻的“理喻”。因此我们可以说,宗教尤其是宗教性所适应的,就是人性对于终极关怀的需要。终极关怀与科学、哲学不无关系,但是,只有在宗教中才作为根本而存在。这无疑是一种真正伟大的创造,人性的创造。人类正是出之于这一超越才创造了宗教,因此也通过这一创造而创造了自己。意义在想象中编织,生命在宗教中转换,失乐园之后的自由在终极关怀中获得(失乐园之前的自由没有意义),雅典也在“适应”中最终臣服于耶路撒冷。这创造,就是终极关怀,就是海德格尔所说的使庙成为庙的东西,也就是黑格尔的没有宗教精神的宗教就像庙里没有神的名言中的所指(我们说中国没有真正的宗教,也正因为它缺乏关怀,有宗教但是没有宗教精神)。
声明:本媒体部分图片、文章来源于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权,请联系删除 025-8470736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