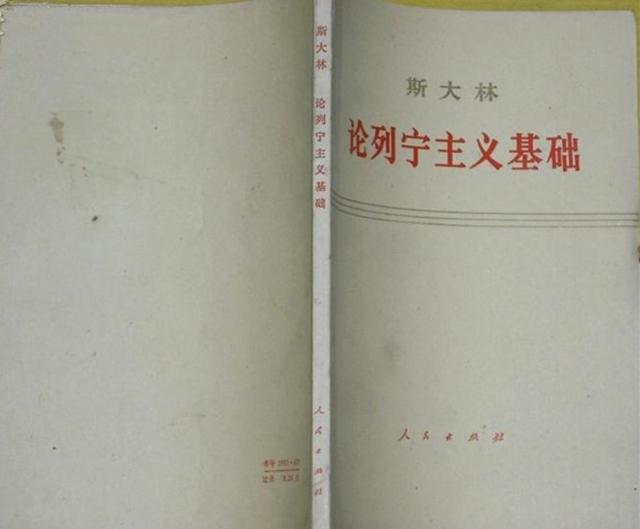但是这些说法都经不起推敲。所谓“逃杨不必归墨而即归儒、逃墨不必归杨而即归儒”只是这些论者的“假令”,而与孟子的说法完全相反。至于说杨墨本皆出自仁义,只是分别“过”和“不及”了些,因而要由孟子来调和“执中”,这与孟子痛斥杨、墨的言辞如此激烈更难合辙。
其实孟子自己在另一处提及杨墨时已经说的很清楚:“杨子取为我,……墨子兼爱,……子莫执中,执中为近之,执中无权,犹执一也。所恶执一者,为其贼道也”。(11) 调和杨墨而取折中之道的不是孟子,而是子莫(12)。对于子莫,孟子批评他“执中无权,犹执一也”,亦即只知折中,不知权衡杨墨之利弊,那就跟走极端一样错误。显然孟子认为,应该比较杨墨而分远近,而不是一味调和。
除此而外,大多数论者都是承认“杨近墨远”、肯定孟子辟墨甚于辟杨的。但是何以如此,则又有多种解释:
程朱之间的宋儒杨时曾说:“禹稷三过其门而不入,苟不当其可,则与墨子无异。颜子在陋巷,不改其乐,苟不当其可,则与杨氏无异。”(转引自朱熹:《孟子集注》)。朱熹对此评论曰:“墨氏务外而不情,杨氏太简而近实。故其反正之渐,大略如此。”(13) 显然朱熹也肯定儒杨较儒墨为近。但“太简”何以就“近实”,朱子语焉不详。
民国年间的郭沫若与当代台湾学者袁保新都把杨朱看作道家,因而把“杨近墨远”解释为“儒与道之比较相近”,(14)“墨家的热情……必然要再走回人群,必然会走到儒家这条路向上去。”(15) 只是,杨朱与道家虽有某种联系,尤其是杨朱后学与秦以后的道家渐趋合流(如《列子·杨朱篇》所显示)大概是事实,但在孟子的时代要说杨朱就是道家,显然过于牵强,因为那时的道家同样热心于拒杨墨,说“敝跬誉无用之言……杨墨是己,”(16) 甚至要“钳杨、墨之口”。(17) 更何况按二程的说法,杨道虽有联系,杨儒、墨儒更有联系,论其远近何必假途于“道”?
还有些现代学者把儒家,尤其是思孟一派的儒家作了“个人主义”化的解释,认为“杨近墨远”是因为孟子与杨朱都主张利己。只是杨朱只求利己不损人,而孟子要求利己亦利人。但墨翟则要求“舍去我字,损己利人,当然为孔门所不许”。所以“孟子认为他(杨朱)的学说,高出墨子之上。”(18) 但是这种对古儒的理解是十分成问题的。孔孟都有许多克己复礼、舍生取义、杀身成仁之类的说法,论者或可责其虚伪,但责其公开反对舍己为人、甚至恶舍己为人甚于所谓自私自利,则殊无根据。
拔一毛之权属谁:古儒论个人及“天下”皆非本
本着“注唯求古”的原则,笔者认为唯一真正能与孟子的原文对上号的解释是汉儒赵歧之说。赵歧在“逃墨必归杨”条下注曰:“墨翟之道,兼爱无亲疏之别,最为违礼;杨朱之道,为己爱身,虽违礼,尚得(受之父母)不敢毁伤之义。……故曰归:去墨归杨,去杨归儒。”(19)
这个说法在宋儒孙奭的疏中又得到进一步发挥:“墨翟无亲疏之别,杨朱尚得父母生身不敢毁伤之义。儒者之道,幼学所以为己;壮而行之,所以为人。故能(逃)兼爱无亲疏之道,必归于杨朱为己;逃去杨朱为己之道,必归儒者之道也。”(20)
赵歧的说法之所以值得重视,不仅因为其注早出,更因为它实际上是把“杨近墨远”当成一个权利(right,或曰“正当性”)问题,而不是如“儒道相近”说所言的学派问题或“利己利人”说所言的狭义伦理问题。从赵歧到孙奭的论者虽然并无强调right意识的自觉,但所谓“受之父母,不敢毁伤”的意思很明确:拔一毛以利天下这事不是不该做(显然是该做的),而是“不敢”做。为什么不敢?当然不是怕疼,也不是怕吃亏,而是因为我的“身体发肤”包括“一毛”在内,都是“受之父母”而并不属于我自己,因此没有请示父母我就无权这么做。墨子目无父母,在孟子看来自然大逆不道。但是如果父母许可,或者父母授意,这事当然要做了。杨朱“爱身”如果是为父母,当然不错,这应当是孟子看来其比墨为“近”之理由。但是他这“爱身”是“为己”,似乎拔不拔一毛全凭己意,这就“违礼”了。在这方面孟子认为杨墨都是“邪说”。
可见按赵歧的解释,古儒实际上不是把“拔一毛以利天下”的问题理解为应该不应该“为”的问题,而是谁有权利“为”的问题。笔者以为,在孟子“辟杨墨”的战国时代,社会变迁所涉及的最根本性的问题就在于此。
我们知道杨朱“为己”之说被后世诋之为自私自利(孟子也是发动这种诋毁的责任人之一),正如孔孟“不敢毁伤”之说在现代曾被诋为贪生怕死的“活命哲学”一样。但是这两种诋毁之浅薄固不足论,而识者包括孟子自己,乃至像二程那样的儒家后学,实际上都知道真正的分歧并不在此——否则他们决不会说“杨子为我亦是义”。拔一毛以利天下,值得不值得?应该不应该?我想一般人,包括杨朱,都不会说不应该、不值得。然而,我愿意为天下拔己一毛是一回事,别人(包括众人)以利天下为由拔我一毛是另一回事。真正的问题在于:谁有权利作出这个抉择?“拔一毛”的权利属于我,属于我的家庭家族,还是属于“天下”或社会?
近代以来多有为杨朱辩诬者,认为杨朱之说是个人权利观念在中国文化中的滥觞。的确,从现代观念视之,如果以“一毛”喻个人之权利,则但在“群己权界”之己权内,他人及公共权力不得以某种理由,包括“利天下”之理由辄行剥夺。至于我行使己权,自愿为天下利,则“拔一毛”固无足论,即抛头颅、撒热血,其权在我,我自慷慨为之,何其壮哉!
声明:本媒体部分图片、文章来源于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权,请联系删除 025-84707368。